订阅
|
问卷投票显示投票结果 作者:东旭 “糟了,这份名单恐怕会害了我!” 1948年12月25日,浙江省府主席官邸,陈仪手里拿着一份密电,对自己的秘书忧心忡忡地说。 那封密电,是我军公布的蒋军战犯名单。 陈仪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这份共43人的战犯名单上,各省的主席全都上榜,唯独自己的名字不在上面。 按照我方的说法,这些战犯是要被送上审判台的,陈仪没有上榜应该感到庆幸,为何反而如此担忧? 还有,我军为何没有把陈仪的名字列入战犯名单? 这一切,还要从一个叫胡允恭的地下党员说起。 胡允恭,(曾化名胡邦宪)安徽长丰县人,1924年就加入组织。 后来他被组织调往广州,到黄埔军校,在周公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 1948年7月下旬,在上海居住的胡允恭夫妇突然接到华东局城工部负责人吴克坚的指示,要他们马上到杭州去,策反陈仪率部起义。 陈仪不但是浙江省主席,还是浙江保安司令,如果能起义的话,等于在蒋氏背后捅刀,后院点火。 更重要的是,陈仪如果被争取过来,还可能带动京沪警备总司令汤恩伯起义,那样对蒋氏将是致命一击。 胡允恭和陈仪是什么关系,如何有把握策动对方起义? 1883年出生于浙江绍兴,1902年东渡日本进入振武学校第五期炮兵科,和蒋氏是同乡加同学。 因此,蒋氏对陈仪非常器重,1926年蒋氏上台前就是国民革命军十九军军长。 胡允恭和陈仪在北伐时就认识,算是陈仪的“亲信”。 陈仪无论是1938年担任福建省主席,还是抗战胜利后出任台岛军政首长,都将胡允恭带在身边,委以重任。 陈仪把胡允恭看作智囊,对他言听计从,如果游说陈仪,影响很大,成功率很高。 还有,陈仪主政台岛的时候,发生了震惊中外的“228事件”。 陈仪在事件中处置不当,犯下重大失误。 作为智囊,胡允恭掌握了太多秘密,等于拿着陈仪的把柄。 内幕一旦公布,陈仪的前途将会被断送,还可能被蒋氏严惩。 因此,胡允恭更有把握让陈仪就范。 还有,蒋氏虽然对陈仪信任,陈却对蒋非常失望,并没有打算为其殉葬,言语中流露出对我方的好感。 这一切的一切,让我军觉得策反陈仪可能性很大。 至于汤恩伯,跟陈仪关系也很特殊。 陈仪担任浙军第一师师长的时候,汤恩伯是他手下的一个小排长,默默无闻。 1922年3月,汤恩伯考入了日本明治大学法科,也是在这里认识到了陈仪的干女儿王竟白。 然而汤恩伯家境贫寒,穷得叮当响,正在日本上学的时候学费没了。 汤恩伯无奈,在1924年夏天回国筹集学费。 然而人到落魄的时候,谁都不想帮。 就在这时候,陈仪雪中送炭,对汤恩伯伸出援手。 陈仪慷慨地说:“你在日本的学费包在我身上了,不过你要学军事,在中国学法律没用。” 陈仪利用自己在日本的关系,保送汤恩伯上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第18步兵科学习。 1926年,汤恩伯学成之后,自然成为陈仪的亲信,被任命为第一师少校参谋。 为了更紧地抓住陈仪这个高枝,汤恩伯甚至休掉了糟糠之妻,迎娶了陈仪的干闺女王竟白。 如此一来,陈仪也算是汤恩伯的义父或者岳父。 正是陈仪把汤恩伯推荐给了蒋氏,让他飞黄腾达。 就凭这层关系,陈仪如果反正,汤恩伯似乎没有理由不追随。 汤恩伯 因此,接到组织上交给的任务,胡允恭也觉得胜券在握,就决定去策反陈仪。 就在这时候,恰好陈仪捎信来了,要他到自己身边工作。 于是胡允恭夫妇动身去杭州,开始了他的策反之路。 由于是陈仪的膀臂,胡允恭夫妇一到杭州就受到陈仪的热情欢迎。 当晚,陈仪在西子湖畔楼外楼酒家设宴,为老部下接风洗尘。 酒宴上两人共忆峥嵘岁月,感慨万千,滔滔不绝。 酒逢知己千杯少,二人推杯换盏,不醉不休。 酒酣耳热,直性子的陈仪就开始说心里话:“说实话,我对前途非常悲观;小蒋(陈仪比蒋氏大4岁)连崇祯都不如,众叛亲离了。” 胡允恭借机说道:“是啊,我也有同感。” 陈仪不无忧虑地说:“像我们和对方打了这么年仗,对方能不咎既往?” 胡允恭说:“他们对待起义人员非常宽容,吴化文跟他们不是也有血海深仇,起义后不是也受到重用了吗?” 胡允恭说的吴化文,有“小吕布”自称,先投冯玉祥,再投蒋氏,后来还投靠汪氏当过汉奸。 济南战役之前,吴化文身为66军军长,率领两万人起义,随即被任命为解放军35军军长。 这么一说,陈仪动了心,他压低声音问:“允恭啊,你到底是不是对方的人?你可以代表他们?” 胡允恭说得意味深长地回答:“我不是,但是我有朋友是,他说话算数。” 陈仪听了面露欣喜之色,兴奋地说:“如果这样,再好不过……我已狠下心来,为浙江和平解放尽点力,不过你要保证我的安全!” 胡允恭一听心中暗喜,在几天后悄悄返回上海,向组织上作了汇报。 组织立即将此情况上报总部,同时授权胡允恭回杭州直接与陈仪谈判。 胡允恭再次见到陈仪之后,亮明了自己的身份。 陈仪大喜,双方开始实质性的谈判。 比如起义后保安团队如何安排,准备迎接人民解放军过江,如何释放在押的犯人等。 双方的谈判非常顺利,陈仪非常兴奋,似乎看到了和平曙光,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中。 他丝毫没有注意到,一双阴险的眼睛早已在黑暗中盯上了他,就像老虎窥视着猎物,等时机一到,进行致命一扑。 这个人,就是军统特务骨干毛森。 毛森,浙江江山人,与同乡毛人凤、毛万里并称为“江山毛氏三杰”。 毛森早年毕业于浙江警官学校,追随戴笠多年,是军统骨干,他诡计多端、心狠手辣。 毛森在抗战期间到敌占区搞破坏,弄得上海鸡犬不宁,日伪仓库被炸、铁路瘫痪、汉奸遭狙杀…… 毛森 他曾经两度被日本人抓获,但是都神奇脱险。 不仅如此,在日本监狱里毛森仍然大显身手,指挥了别动队除掉了军统叛徒李开峰。 1946年,面粉大王、民族资本家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被绑架,赎金支付了,人质也放了。 但是毛森不肯罢休,竟然神奇破案,抓获绑匪。 从上述事例不难看出,毛森的能力非同小可。 他当时的职务是浙江省警保处长,手下人马数千,虽然人数不多,但个个训练有素,都是精英。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陈仪虽然久经官场,却忽略了毛森的存在,不能不说是一大失策。 毛森凭着敏锐的嗅觉,感到陈仪有异,浙江怕要出乱子,他随即向保密局长毛人凤做了汇报。 毛人凤立即下达密令,授权毛森对陈仪进行密切监视。 毛森随即挑选了20名精干特工,一天三班倒,对陈仪的官邸进行24小时监视。 进出陈仪官邸和省政府的胡允恭,也同样被监视和跟踪。 毛森认为,胡允恭在战局不稳的时候来到陈仪身边,肯定别有用心,决不是想利用老关系当官。 为了试探陈仪是否有二心,毛森在1948年11月将一份浙江地下组织成员和进步人士的名单递了上去,建议就地枪毙。 然而陈仪看后,并没有批准处决,而是批复道“一律送犯人去反省院”。 不仅如此,陈仪还秘密下令将10余名“证据确凿”的“要犯”交富阳绅商界父老“具结领回,管束教育”,其余被捕者则一律就地释放,既往不咎。 这一系列的举动,让毛森更加确认陈仪被“染红”,坚定了监控陈仪的决心。 而陈仪并没有重视这个对手,反而将毛森的杭州警察局警保大队改编为省警保处警保总队,并扩编为两个大队,将自己的十几名亲信安插进去。 不仅如此,陈仪还向亲信下达一个死命令:你们不得镇压工人学生,除了我的命令,警保总队不听任何人指挥…… 这让毛森心里犯嘀咕,觉得陈仪“心怀不轨”。 尽管如此,他只是怀疑,并未有真凭实据。 之后我军公布的战犯名单,引起蒋氏怀疑。 这一期间,为了准备起义,胡允恭就住在陈仪官邸里。 陈仪非常关注外部形势,每晚都派人手抄我方发布的电讯。 1948年12月25日,秘书拿着一份名单走了进来。 陈仪一看,是我方公布的43名头等战犯名单。 他戴上老花镜,看过之后大吃一惊,名单上各省负责人都赫然在列,唯独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 他让胡允恭看了几遍,依旧如此。 陈仪不禁暗暗叫苦,对胡允恭说道:“这份名单对我不利,怕会害了我。” 果然,1949年1月21日,蒋氏被李宗仁、白崇禧逼迫下野,来到奉化溪口后,随即紧急召见毛人凤和毛森,开门见山地说:“看来公洽(陈仪字公洽)是铁了心背叛,辜负了我的他的信任,如何处置,你们可以见机行事,不必请示我。” 这边陈仪对此则毫无觉察,仍在紧锣密鼓地部署起义。 他通过胡允恭和民革的郑文纲转告中共方面:解放军渡江后,请速派一联络参谋携一本密电码来杭州,以便和我军进行联络。 与此同时,陈仪对汤恩伯的策反也在积极进行中。 1月27日,一个30出头的男子出现在上海警备司令部,说是有封信要交给汤恩伯。 汤恩伯一看这人自己认识,是陈仪的外甥丁名楠。 信的内容不用说大家也猜得出来:准备起义。 陈仪虽然对汤恩伯有恩,但是汤没有打算追随陈仪。 汤恩伯看来,陈仪不过是自己的引路人,真正让自己飞黄腾达的是蒋氏。 1933年汤恩伯修祖坟的时候,蒋氏亲笔为墓碑题词。 抗战胜利后,蒋氏委任他为南京警备司令,后来又任命他为陆军总司令。 南京失守后,蒋氏又任命他为京沪警备总司令,负责上海防务。 汤恩伯认为蒋氏对自己有知遇之恩,死心塌地要效忠蒋氏。 对陈仪的策反,他采取了拖的态度,回复说自己不日将去杭州,跟陈仪面商。 可是,一周过去,陈仪也没有等到汤恩伯。 胡允恭目光敏锐,料到汤恩伯不能指望,但是陈仪仍然心存幻想,再次命丁名楠带上自己的亲笔信去见汤恩伯,并介绍胡允恭一同前往。 陈仪是老江湖,也为自己留有后路,信件的内容较为暧昧,一般抓不住把柄。 比如第一封信的内容是: “一、军队宜紧握;二、待遇宜提高;三、驻地宜规定;四、军风纪严肃;五、沪防御工事宜停止,已征集修建之材料酌量归还;六、营房宜多建;七、征兵宜减少或竟停征;八、军事机关宜紧缩,事权须统一。” 恩伯弟台如晤: 但是第二封信就有点露骨,内容是: “兹丁名楠来沪,面陈一切,请予洽谈。再旧属胡邦宪,拟来晋谒,请予延见。至胡君经历,嘱由名楠奉告,并希台洽为荷。” 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能从“至胡君经历,嘱由名楠奉告”这几个字中看出端倪。 汤恩伯这次态度鲜明,就是不会起义。 他给陈仪的回信是这样写的“但我必须考虑,陈先生也要考虑”。 而且汤恩伯警告丁名楠,下次不要再来了。 胡允恭感到情况不妙,随即和上海地下组织负责人吴克坚联系,询问详情。 不问则已,一问大吃一惊:汤恩伯已经出卖了陈仪。 事不宜迟,胡允恭冒着生命危险悄悄去了杭州,来到陈仪官邸,告诉陈仪:“事情有变,当机立断。” 陈仪却非常自信地说:“谁出卖我,汤恩伯也不会。” 胡允恭听了暗暗叫苦,只得立即离开陈仪官邸,逃出了杭州。 1949年2月17日,蒋氏终于出手,已迁广州的行政院宣布改组浙江省政府,免去了陈仪和其亲信的职务。 陈仪这才慌了手脚,在2月21日晚抵达上海多伦路志安坊私宅。 他没有注意到,保密局的毛森全程“护送”,尾随他到了上海。 两天后,毛森率领一队特工和宪兵闯入陈家,将陈仪的卫士、副官缴械扣押,然后逮捕了陈仪。 1950年6月18日,陈仪在台北被蒋氏杀害,终年67岁。 在出卖恩师的同时,汤恩伯向蒋氏提出一个先决条件:保证陈仪的生命安全。 但是蒋氏也有个条件,那就是陈仪必须认错。 陈仪被关押期间,财政部长俞大维和参谋总长林蔚,以及陈仪的众多部属故交曾先后探望过他。 说是探望,其实就是规劝。 他们暗示,陈仪只要向蒋氏认错,就能重获自由。 但是陈仪说:“我为国为民,何错之有?” 蒋氏听了恼羞成怒,下令处死了陈仪。 其实陈仪的死元凶是保密局的毛人凤和毛森,因为他和军统有血海深仇。 1938年,陈仪主政福建的时候,曾经以“破坏抗战”为名,不顾蒋氏“刀下留人”的指令,处死了军统福建骨干马超。 自此之后,陈仪算是跟军统结下梁子。 当然,如果汤恩伯不点头,毛森也不敢在上海抓捕陈仪。 但是陈仪执迷不悟,到死也不相信是他的学生出卖了自己。 他对记者说:“我与恩伯的关系如此,他要是不赞成,可以直接建议我停止一切活动,何必出卖我?” 汤恩伯 而汤恩伯也怕背上出卖恩师的恶名,一直在为自己辩护。 1950年4月,台岛方面审判陈仪,在审判席上汤恩伯出庭作证时说:“我对犯人陈仪,一生受恩深重,难以言喻,正图报不暇,何肯检举他?” 总而言之,陈仪太过自负,缺乏应有的警惕,最终事发身亡。 最初胡允恭曾经对他说过这么一句话:在蒋未下手之前,及时举起义旗,否则机宜坐失,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可惜一语成谶,陈仪壮志未酬,叫人唏嘘。 陈仪起义虽然功败垂成,但是陈仪、胡允恭为了江南人民免于战火,不计个人安危做出了不懈努力,依旧值得颂扬。 我军公布的战犯名单(1948年12月和1949年1月曾经公布两批一共57名,都没有陈仪的名字),虽然不是陈仪暴露的主要原因,但名单中为何没有陈仪,也成了难解之谜。 (1950年,胡允恭任福建教育学院副院长。全国院系调整后,调到南京大学历史系执教,1981年去世,享年79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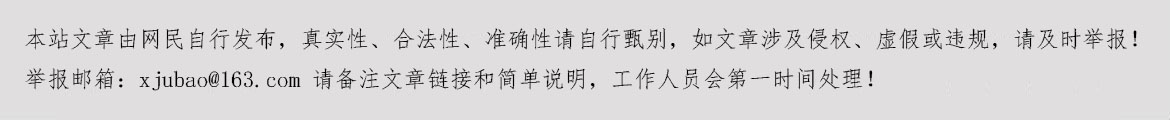
|
|
10 人收藏 |
 鲜花 |
 握手 |
 雷人 |
 路过 |
 鸡蛋 |
收藏
邀请